陈染:麦穗女与守寡人
陈然:麦穗姑娘和寡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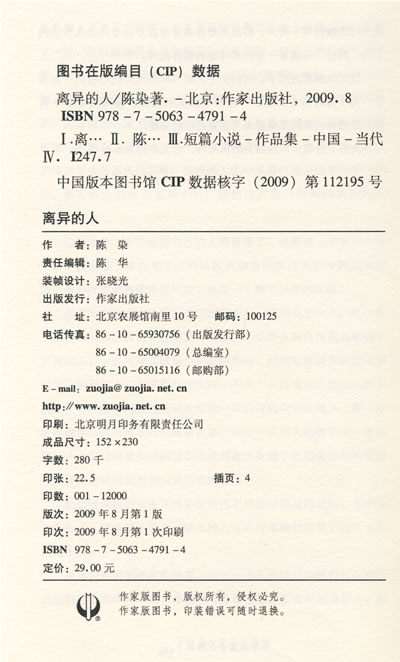
灵魂钉子
我们在黑暗中从颖子家的四楼走了下来。在深夜已经是2:27了。这一天是4月10日,是我的个人周年纪念日。实际上,在我拼命留下并挽救垂死的,糟糕的婚姻生活和另一种绝望的情感生活并彻底失败之后,我死了。
破碎的九月藏在那个人的身后,让我秘密地离开了我,我的心永远无法表达出来。由此,我也明白,这个世界上可以尖叫的绝望实际上是一种激情。但是它只能被密封在我的心底,你必须假装在所有人面前什么都没发生,你只能偷偷地藏在被子里,那种哭泣才是真正的绝望。
9月之后,我不再谈论周年纪念日。
我的一个充满诗意,热情而美丽的女友Yingzi带我到她家,度过了这一天,我必须独自承受。
当颖子送我到楼下时,我们牵着手走在黑暗的走廊上。正是在这一刻,我突然发现,在这个世界上,有两只手像玉一样冷。这一发现使我感到此时的世界不再孤单,而此时的世界尤其温暖。
我一直认为,除了人类可以说的眼睛之外,人类的手是最准确的语言,而嘴唇的声音只会帮助人们进行精神交流。如果一个人能读懂您所握住的另一个人(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的手的语言,那么您的内心和情感就非常接近。
颖子有一个温暖的家和一个温暖的丈夫。 4月10日下午,我来到了颖子的家,那里充满了稻草般的浅黄色阳光和芬芳。颖子的家充满了女主人太妃糖的温暖红色气氛。
我在她的房子里坐了一个小时之后,有一秒钟很奇怪。我突然失去了理智,错过了昔日成群的妻子和conc妃的踪影。突然,我感到生活异常美好。我认为英姿和我将都是人类女性。历史上最富有同情心和关怀的“同情者”。堕落的那一秒完全归因于我破碎的单身女人一生的情感空虚,以及我梦dream以求的梦游思维方式。但这只是堕落的一秒钟,转瞬即逝。一秒钟后,在我眼里,颖子那位温柔睿智的绅士变得陌生而遥远。这种陌生和偏僻的感觉源于我内心对鹰子的坚定不移的忠诚,以及我情感方式上不合时宜的单向经典感觉。
当英姿牵着我的手送我到楼下时,大约是半夜2:28。大楼前的开放空间散发着孤独的黑暗,就像东方女性纠缠着我们的长长的黑发。在凌晨2:29和凌晨2:30之间发生了一些事情。当时莺子在跟我说话。也许是在问我是否很冷,也许是在问我对她丈夫的感觉。我什么也没听到,只是微弱地感觉到,Yingzi柔和的声音在夜风吹过的冬衣和皮肤切开的身体之间空荡地滚动着。我的理由要求我去听并判断声音的含义。但是我混乱的大脑突然在我思维边缘的一个钉子孔上生锈了。漆黑的夜晚使我的想象力变成了一把锤子,追着它,敲敲指甲而没有任何声音。
因此,我看到了一个巨大而令人眼花nail乱的钉子,像一块立在五六米之外的墓碑。钉子后面是一个又高又重的男人。他半蹲,因为他想做他的色情面孔。暴力的目光藏在指甲后。指甲急剧而严峻地靠近。在他的带领下,那个人走近我和英姿。我抓住英姿,迅速转过身来。整个世界都被颠倒了,这再次让我惊呆了:我发现我身后的景象是我面前景象的复制品。逼迫的钉子自动出现在我们的身上,钉子的后面是另一个长期计划的可怜的钉子。男人。
我担心英姿发现这起突发事故时会惊慌失措,对本人的惊恐反应,对我的反馈甚至更大的恐惧。
当颖子什么都不懂时,我们的前胸和下背部牢牢地靠在两个急切的指甲上,两人的淫秽的笑容中露出了洁白的牙齿。在这个深冬的夜晚,明亮的牙齿确实是一束白光。
如果我一个人,我会很顽固地放手。与狼作战是愚蠢而徒劳的。我知道,当一个人用钉子作为谋杀武器时,他只想要我的身体。我身体,手,脖子和钱包中的贵重配件无法丝毫改变,也无法挽救我。除了等待死亡,别无他法。但是此刻,颖子天真地站在我旁边,就像一只迷人的羔羊,什么也没发现,也没有自卫的样子,一头产妇的麦穗,脖子在九月的天空的草坡上起伏。结果,我的莫名其妙的责任和无能为力的力量被鬼送了出去。
我对两个令人信服的指甲说:“无论我走到哪里,我都会和你一起去,但你必须让她回家。”
两个指甲暗暗地看着对方,微笑着:“为什么?”
是不是我是一个寡妇,专门被绑架和抢劫。我出生于这种材料。我早已习惯被洗劫,我的心早已被坚硬的厚茧覆盖,任何穿透都很难真正触动我。
这两个人像指甲一样剧烈地咳嗽:“如果不呢?”
“没有房间。碰她,我会杀了你!”我说。
还有一个特殊而紧急的微笑,像钉子一样。
然后,四只男人的手像鹰爪一样伸出到我们的胸部和腹部。焦急地,我把那个男人踢到了小腹前面。
砰,强迫的钉子落在那个男人身上。接下来,我以闪电般的速度抓住了躺在地上的锋利钉子,转身刺穿了我身后腹腔中的那个人。一团黑血像浓烟一样喷出,与动荡而稀薄的夜晚融为一体。放血后,男人立刻缩了缩,他的欲望和血肉从受伤的钉子孔里滴了下来,放开了。过了一会儿,他就像一个高腰的皮靴,在下雨天像粉末一样掉进泥里,慢慢躺下……“你在想什么?”颖子把我的灵魂拉走了。
在这里,我发现英姿和我已经在黑暗狭窄的开阔地面上堆满了瓦砾和堆积在我们脚下的废物。它们就像漂浮在水中的物体,不断地上下闪烁,发出嘶嘶的呼吸声。一朵淡淡的花和叶子的紫丁香树在我们的身旁旋转着,颖子散发出淡淡的紫丁香树的芬芳。
满月的街道早已摆在我和英姿的面前。我不知道我们是朝着它走还是正面临着我们。
这时,我迷迷糊糊。我和颖子在一起看着我们的脚。
我安定下来,隐约地看到我们脚下无声的黑色橡胶靴。
两个租金陷阱
“你听说过吗?”颖子的声音终于冲进我的大脑,在凌晨2:30周围被薄雾笼罩。
我笨拙地摇了摇衣服,似乎要摆脱血腥的痕迹,“你说什么?”
“我可以问你听吗?”颖子说。
“嗯……我只是……”我的脑袋一片空白。
“你在想什么?”
这时,我的思绪慢慢回到了颖子的声音中,我发现了与她的交集。
“你在想什么?”颖子说。
“营子,你注意到大楼前面的空旷地太黑了,太恐怖了。我担心你送走后我会怎么回来?”
“没关系。我对这个地方很熟悉。”颖子无动于衷。
“您没有发现吗?这个世界上存在阴谋,尤其是在您认为没有问题的地方。例如,每天穿过的墙壁上隐藏着一扇斑驳而安静的窗户。您隐藏在其中一个微笑的背后您组织中最熟悉和最好的朋友。”
“别那么紧张。”颖子装作很镇定。
“对于脆弱的动物,生活充满陷阱,必须时刻提防。”
“这又来了。您何时想重复“动物世界”中的这一行?那是行!您必须保持生活的事实和无数的想象力经常分开才能放松。”
这时,我们已经完全穿过了月球瘦弱角落下方的无人野地。在黑暗中,我觉得英姿和我永远是两根牢固的女性骨头,彼此相连。腿和脚挥舞着自己的力量向前走,但是脚步像无用的话语一样悄悄地悄悄传到了位。巨大的黑暗无情地慢慢地掠过了我们,枯叶在树枝上摇曳着风桨,推动我们前进。晚上的运动缓慢,我们的髋骨不时发生碰撞,夜晚发出了铁锈般的吱吱声。我想象这个垂死的领域一定经历了无数次鲜血而可怕的战斗和历史斗争。这些人的尸体躲在我们周围,清晰可见。在他们的身上,尖锐的武器,例如巨大的钉子,已经在延时中腐烂成一堆废铁,但巨大的死者骨骼上的目光却盯着每一个经过它们的妇女。埋伏的长发准备好进行无形攻击。
在建筑群的出口处,那是一扇旧木门,半开着。我一直相信,半开放,半封闭,半推挤和半契约的任何一种存在都是人类想象力的最大动员和诱惑。无论是真理还是女人,完全裸露和穿着模糊薄纱所产生的引力之间的区别就是我。有力的个人经验证明。
潜伏在半盖的木门后面的想象力完全占据了我一段时间,门外似乎有柔软的脚步声。
我总是对隐藏的门和远方看不见的脚步感到莫名的恐慌。我认为这是一个潜在的危险,潜在的危险,死胡同或生命的诱惑。人们走进空旷的黑墙上。似乎总是有人把砷放到你的面粉旁边。但是,如果您打开或关闭所有门,让脚步声传到您的眼中,焦虑就会消失。我知道,成年女性很难表达这种恐惧,但我无法控制自己。
我握着正在接近木门的颖子的手臂。
“小心,危险!”我说。
“你怕什么呢?”颖子还是很粗心。
暗褐色的木门已经站在我和颖子的面前。它在颤抖,巨大的身体看起来喘着粗气。
当我们走出木门时,什么也没发生。我认为这确实是一个奇迹。
“看来我必须送你回家。你在担心什么?你的手在颤抖!”颖子说。
一个男人愚蠢地走在我们面前。我发现他的脚步不同于我和英子的脚步。这一步无形地违反了宁静的夜晚,而我和英子的脚步使夜晚变得安宁。
我认为这个人可能是刚才看不见的足迹的创造者。
“我什么都不怕。”我说。
我知道我唯一的恐惧是我的心理。
我和英姿走出旧木门后,一辆黄色的出租车从黑暗中驶向我们,就像耀眼的黑光使人们想知道它从何而来。
司机温柔勤奋,看上去像个普通的老实人。当他在车上向我们打招呼时,他谦虚勤奋的态度使我可疑地路过:这是蓄意和期待已久的阴谋。
晚上在这条安静而荒凉的街道上,碰巧碰巧到我们离开时马上迎接他的车吗?我宁愿相信一个看起来像坏人的男人。
我想阻止英姿上车,但英姿的一只脚和她那开朗的小帽子已经到达了出租车的后门。所以我不得不拼命地打开前门,坐在司机旁边。我认为对我们来说,串联坐着可能更安全。大约是凌晨2:31。
汽车开动时,我听到了莺子的尖叫声。我立刻转过身来。
这时候,我和英姿找到了另一个好男人,坐在后座角落的阴影中。他只有一半的脸和一只眼睛。
一切都结束之后,我不知道这个男人的另一半脸是否被埋在了阴影中。
我看到他的眼睛就像是最深情的老黄牛的眼睛。它使我想起到处都是田园绿草,阳光和田园歌曲,还有一头红嘴鸟在亚麻棉田中和平滑行。但是,我从另一半脸上看到了另一件事:他的身体实际上只有一半的生命。
亲身经历告诉我:让人们无需判断就值得信赖的原因一定是美丽而诱人的误解。这是一个被玫瑰围栏覆盖的陷阱。现在,颖子和我一直在不可挽回的小偷船上。
这辆车就像是夜间自动爬行的坟墓,使人们感到自己进入了一场噩梦而无法控制。
我注意到,驾驶员透过镜子看不见他的脸的后半部分。
一半的脸说:“走同一条路。”
司机说:“没问题。”
我想,他们已经开始交换代码字了。
车窗外有一股类似金属的尖锐风,我听到高音中的“时间”在颤抖,就像小提琴手一样紧张,在我的耳鼓上滑动得很紧。像火柴盒一样的建筑物迅速向后移动。那些沉睡在市区的建筑物,因为它们高耸入云,使人们感到自己总是充满惊慌和鬼魂的能量。
我注意到,我旁边的驾驶员有一双凸出的眼睛,就像甲亢患者,黑色的眼球从他过多的白皙的眼睛中伸出来,他随时都可以射出并深深地陷入我和英姿。进入体内。我还注意到他瘦脖子上的一条蓝色静脉突然暴露出来。我想起了这种脉络。
“你想转弯吗?”我旁边那个鼓鼓的司机再次透过镜子看着我身后的半张脸。
我很担心。我认为鼓鼓的字眼总是暗示着颖子和我不明白。
作为一名熟练的出租车司机,他不知道如何到达我和颖子去的地方吗?我是否在考虑“转弯”,“转弯”或“绑架”一词?我回头看了看颖子,她的脸慌张,身体倾斜,坐在后座的拐角处,离脸的一半尽可能远。
我装作很平静,对她说:“它来了。”
这时,汽车撞上了刹车。我的胸部撞到了我面前的坚硬桥梁。同时,我听到应子东严重摔倒在前后排座椅之间的挡板上,随后发出严厉的叫声。
“你在做什么?”声音来自我的喉咙,但不再是我的声音。
伸出眼睛,微笑着,“出事了。”
一半的脸在阴影中闷闷不乐地说:“调那个。”
于是,他摸索着压了一下,用脚踢了桥下的一个家伙。我隐约看到一个闪亮的钉子从驾驶座下面滑到我的脚上,它眨着眼睛,嘲笑我。我保持沉默,慢慢地将一只脚移开,踩到脚下。
汽车再次不自觉地发动,平稳行驶,好像刚才什么也没发生。
我从眼角看到Drum Eye一只手握住方向盘,另一只手伸进我的裤子口袋,摸了很长时间,然后拿出一些东西,握在手掌中,并将其移交给我的肩膀。他身后一半的脸。多彩的路灯在他的眼球上闪烁,不断变化的颜色使这双眼球溜了出来。
在我的心中,我持有“ tune”这个词,刚才我一半的脸在说。要调整什么?要调整设备?调情?调情?
这时,汽车驶至明亮的十字路口。尽管仍然没有人,但在十字路口空置的警卫塔使我感到这是一个安全区。
颖子从背后将冰冷的手放在我的肩膀上,对我说:“我们可以在这里下车吗?”
我明白她的意思。
我转过头说:“我们要下车了。”
“我还没到那个地方。”凸起的眼睛和一半的面部几乎一致。
“但是我们只需要在这里下车。”我说。
凸起的眼睛露出蓝色的静脉,细长的脖子变成了90度,凸起的眼睛直接对准了我。他笑着说:“上楼时不要考虑摔倒,要和那个地方说话。”
我割伤了皮肤,觉得他的眼睛从眼窝里突然冒出来,射入了我的身体。
“你让我们下车!”我嘶哑地大喊。
凸起的眼睛再次微笑着,“如果没有呢?”
现在,他一半的脸闷闷不乐地用他的半衰期将英姿的手拉到我的肩膀上。神!他的半个鬼魂已经碰到了颖子。
我一团糟,只听见脑海里传来巨大的雷声。沉思桥上的嘎嘎作响的手也空了。
“十三点,十二点,十一点,十点,九点……”我心里开始倒数,等待绑架的命运在我骨头深处的最后时刻。
出租车在一个明亮的十字路口处驶出街道,进入一条狭窄的黑色长廊,道路两旁的淡黄色路灯令人迷惑。我知道路灯是黑暗中的唯一见证者,长期以来习惯于像许多人一样撒谎。它不再代表光。
“八,七,六,五...”
...嘿,黑色的楼梯走廊...长长而狭窄的地面...在粉状的雨水中粘死的橡胶靴子...被栏杆包围的垃圾...睁大眼睛凝视在我和英兹坎(Yingzikan)骷髅走过的路上……那扇脚步声传来的隐形旧木门……淡淡的丁香树上没有花朵和叶子的英国人的香气……钉子敲打着灵魂的声音。 ..…
时间完全回到我的心中,退回到早晨的2:29至2:30。
“五,四,三,二...轰……”
一声巨响震撼了我永恒的夜晚!
当英姿和我从倾覆的火球中逃脱时,在浓烟中,我看到凸起的眼睛上露出的蓝色静脉和狭窄的脖子上喷着一股鲜血,像是一股血流,落在方向盘上。在他身后是半条命,半张脸缠绵。
“你被谋杀了!”在这个暮色的冬天,英姿的尖叫声在陈旧的街道上回荡。
像两张白皮书一样,我和Yingzi醒目地站在铜鼓嘶嘶的心跳上,无奈地颤抖着。
我浑身是血,斑驳。
天哪!从驾驶员座椅下方伸出并被我踩到的钉子像急风一样莫名其妙地抓住了我的手。
三个绑架者
我面色苍白而僵硬,坐在看似雄伟却又肮脏又粗俗的法院大厅里。我的耳朵厌倦了日常生活,嘴唇仍然苍白,似乎仍在呼吸,我仍然在会场感到混乱。
在我旁边是两位纪念性警察。我好几次想伸出手抚摸他们的嘴唇,看看他们是否呼吸出与我相同的热量。他们一定把我当成是瘦弱的黑母马(我穿着老旧的黑色制服,上面有个女囚犯),而且他们强壮的体格可以抚平我。但是我知道所有all绳都无法阻挡我的心!
这样一匹瘦弱的母马,你可以骑着她,肆虐她,鞭子可以征服她的身体,可以让她身上流血的,看不见的伤痕,可以让她的生命永远死去,但是你可以做到。不能动她的心!她的心只能被爱喝醉而死。
法官直立地坐在审判台的中央。他的坐姿使我立即感到自己是一个真正的囚犯。
我的辩护律师在法庭上进行了有条理和混乱的辩论之后,我看到法官终于转向了我。
“你有什么要说的?”
我说:“法官先生,这里确实有绑架者,否则,我怎么能杀人?”
法官说:“那绑架者是谁?”
我一团糟。
我试图回忆起4月10日晚上2:31 AM之后两个男人的每一个动作和眼睛的每一个细节,而提示则指向这些小动作和眼睛的背面。有图像和图片一个接一个地连接到我,像电影一样经过。但是我什么也不能说。
我抬起头,期待地看着颖子。我的眼睛变成了无力而无助的手臂,伸向我所依赖的朋友。这是我能掌握的唯一拯救生命的“稻草”。此时,即使没有这样的人,她也一定会站起来为我指出那个人。毫无疑问。
颖子坐在那儿,她那双深沉,宁静,美丽的眼睛盯着我好久了。由于恐慌,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迷人和迷人,就像一只受惊的麻雀坐在摇曳的黑线上。
我感到遗憾,我宁愿让事情顺其自然,而不是让我的朋友参与。
最后,颖子摇曳地站起来,就像黄昏时的黄色麦苗,整个人像一首爱情诗一样微妙而慌乱,迷茫而绕。她终于举起了模糊但说话的手臂。
手指公正而致命地指向-我!
观众一阵骚动。
当当!阁下两次在桌上轻按“沉默!”
然后,法官的目光再次指向我:“你认为你的朋友是对的吗?”
我的目光从球场上的所有注视中移开,期待着我的嘴唇颤抖,而我的思绪漂浮在等待坠落的所有幸灾乐祸和观众之上的气流中。我没看到任何人除了颖子,我没看到其他人。
一滴不再清晰的泪珠从我那已经远离忧郁的脸颊上滚落下来,就像一朵红樱桃从树枝上成熟落下。我把所有死者的尸体都吞下了复活的泪水。
听众沉默了,死亡空无一人。
最后,我说:“……我愿意……入狱。因为……你听不懂她的话。”
“你无视法庭!我们不明白还有谁能理解?”
“你是一个男人,所以你无法理解它。如果你认为自己理解,那肯定会产生误导。”我说。
“您知道您因故意杀人而受到死刑惩罚吗?”法官继续。
“权力总有理由!'强者'总有权力。”我无法解释。
这时,我的辩护律师再次站起来为我辩护:
“据我所知,法官先生,在此案中,我的委托人的朋友在这里所指的绑架者没有达到'存在'的水平。此外,我有足够的材料证明我的委托人是患有妄想症的患者精神分裂症。”
我看到我的辩护律师从他的文件夹中取出了一块材料,“这是我的客户在1992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写的。在她的家人发现之后,实施没有成功。内容如下:
关于死亡概念
1.方法:两瓶强效安眠药。首先服用7片,当您濒临灭绝时,迅速吞下两瓶。双腿弯曲,躺在右侧,左手自然下垂至胸部,右臂在头下方弯曲。
2.地点:躺在阳光明媚,白雪皑皑的白色或黄色沙滩上,靠近母亲公墓的安静而荒凉的海滨;或沿着柔和的波浪沿着海岸蜿蜒的林荫小径行驶。但不要太靠近大海,而要在一个僻静的地方,在那里您可以聆听和平放松和唱歌的舒适声音。
3.时间:在9月的黄昏,当生命还没有老化时,太阳逐渐向西下沉,天空变暗,世界很快就会被黑暗吞没。这时,善良的人们回到了温暖的房间,没有人会发现一个女人在海边安睡,从未醒来。血红色的九月是一个me子手,杀死了我。那人走了,把世界带走了。
第四,最后一句话:不要对任何人说任何话或照片。话说了,路已经走了。
5.遗产:销毁所有信件,日记,照片,作品手稿,录音带,个人令牌等。其余的留给一个独具特色的天才和奉献精神,不受支持的寡妇。绝不要将遗产遗赠给最后的名声。仅将其献给那些像我一样追求和忠诚于生活的人,但是由于她没有家庭,没有孩子,政府也没有给她房子。
6.死亡原因:我死于我自己的秘密-9月的奥秘。
七。题词:原谅我,我只能躺在这里,用冰冷的身体接受你的拥抱。
1992年9月
“请提交此材料作为记录。”法官说。
我的辩护律师向我发送了材料,并继续说道:“我的客户多次向我提及“ 9月”。可以判断出她对“ 9月”有一个“复杂”,没人知道。我的客户正是这种人这种人通常处于极端艺术和精神分裂症的临界线,在两者之间波动,并且通常不容易区分两者边缘人格人们通常在家庭中患有精神疾病历史,或者在童年时期遭受过性暴力,或者在童年时期父母离异多次离婚。我的客户来自这个背景。”
“有证据吗?”法官说。
“我的委托人的母亲可以证明这一点。另一点是,我的委托人声称她的父母已经去世并且独自一人。这与事实不符,也可以看作是她精神错乱的一种表现。”
法庭上又发生了骚乱。
…………
我最后一次看着英姿,她就像一条无辜的小河,被城市角落里的大批人群抛弃,尽我所能将人们扔进她的河水罐,空烟盒,避孕套等中。推到银行,拒绝理解世界上“阴谋”和“肮脏”一词的含义。她的整个身体变成一棵小白桦树,被每个人眼中顽强的嘲笑所折断,li弱的身体和坚硬的心坐在那里矛盾,困惑和坚定。
她什至不知道刚才那只致命的手指指着我的命运!她不知道
但是,我认识她,非常了解她!
在这个拥挤而密集的大厅里,我知道只有这个指控我是“绑架者”的人才是我的帮凶,而她是唯一的帮凶。
如果您是一位仁慈的法官,请把英姿和我送到两个安全的地方:将英姿送到精神病医院,人们可以学习为自己辩护,以便从诗歌中走出来的她可以理解诗歌和现实。真;把我送进一个封闭的牢房,让世界永远看不到我,让时间成为“九月”之前永恒的石墙。
我知道我的先天等待只是一个只能容纳两三个人的笼子,让我头晕目眩,而一个笼子却在摇晃,折断并举起我。我不要豪华的阳光和金色的沙滩。我对整个世界都没有期望。我只想要笼中男人眼中的鞭子拍打我的温柔和残酷。我担心一年四季都有四处开放的生活,渴望有栅栏。
这时,一个衣冠楚楚的英俊男子从大厅敞开的门后像危险的黑色闪电一样飞翔。我疲惫的心不记得他有多少前夫,也不记得背叛的原因使我们大家都想互相残杀。我只记得我们在动荡的洛杉矶的一个“改变心灵的俱乐部”中彼此消失了。
他严厉地对法官说:“我代表一个男性公民诚恳地问你:给她自由。”
我的身心很清楚。我知道他所说的外在自由是要把我推向更大更深的阴谋和陷阱。
当当!法官终于站了起来:
“该法院将尽一切努力查明或否认绑架者的存在。这是此案的关键。现在,该法院宣布陪审!”
可以等待什么!我对法官的决定不感兴趣。无论我在哪里,我都已经是失去笼子的囚犯了。
那年的九月,我独自一人站在离开我的漫游虎鱼的阴影下。在我眼中,这座城市是一片废墟,它将与你同归于尽。
每个人的眼睛都阻止我哭泣。

 好心情的经典语录
好心情的经典语录 经典成长语录
经典成长语录 问心无愧的经典语录 坦荡做人无愧于心句子
问心无愧的经典语录 坦荡做人无愧于心句子 迎接明天的经典句子 奋斗明天会更好的语句
迎接明天的经典句子 奋斗明天会更好的语句 主君的太阳经典语录
主君的太阳经典语录 盛世嫡妃经典语录
盛世嫡妃经典语录 成功人生规划经典格言
成功人生规划经典格言 2017经典励志格言
2017经典励志格言 墨子经典语录
墨子经典语录 爱神经典语录
爱神经典语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