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从母亲到外遇
于光中:从母亲到外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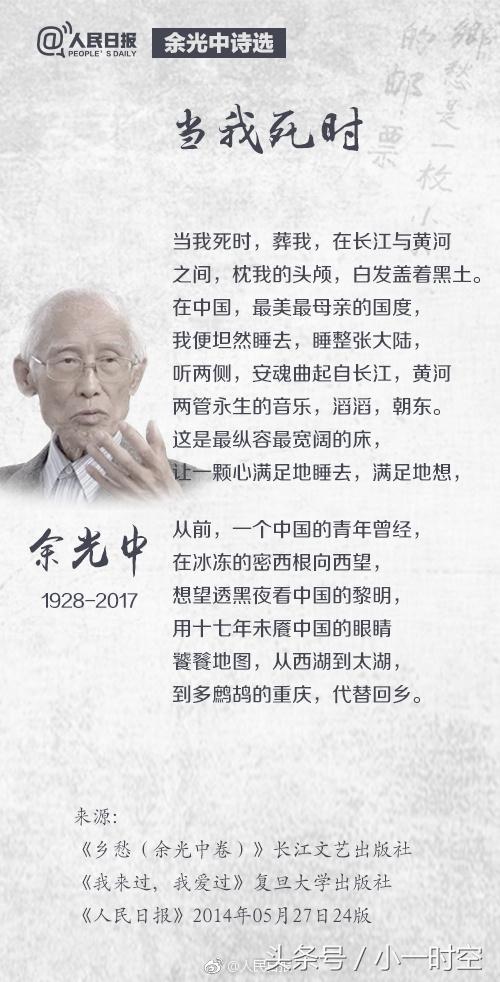
“大陆是母亲,台湾是妻子,香港是情人,欧洲是外遇。”我对我的朋友说过。
大陆是母亲,不用多说。汉唐的灵魂把我烧成骨灰,仍然困扰着这片土地。在那片无尽的家园中,四处游荡的巨龙称她为大陆,强者称她为九州,英雄称她为江湖。不仅是那块大地,还有所有在上面行走并在下面的早晨安息的龙。仍然有几千年来没有执行过的历史,几千年后似乎还没有足够的文化。离开她时我只有21岁,而回到家乡时只有64岁:“当我转身时,风吹起了黑色的头发;回头时,我被雪覆盖了。”长江断奶的痛苦持续了四十三年。洪水泛滥,但没有一滴溅到我的嘴唇上。多年来,我在诗歌中对中国大喊大叫的原因无非是为自己大喊大叫。否则,我真的会迷失自己的灵魂,并被西方的潮流所扫除。
当你的女友改名为玛丽时,你怎么给她唱“菩萨男”?
怀旧是在地理和人类中实现的,但在历史和文化中却是普遍的。有真实的,虚构的,有形的和属灵的,它们必须兼容才能成为三维。怀旧是天生的,自然而然的,与民族主义不同,它起着政治作用。将怀旧与民族主义等同起来,并将政府添加到地理,人民,历史和文化中,是一种“四舍五入”的模棱两可的概念。王朝来了又去了,强加于人的政治无法持久。因此,政治分裂了人们,文化使人们相亲:我们只听说过文化,但从未听说过五华。用武力解放这一点并统一不被视为文化的东西。托马斯·曼(Thomas Mann)逃离了纳粹分子,并在一个外国告诉记者:“我在哪里,那是德国。”他当然说德国是指德国文化,而不是纳粹政权。同样,毕加索因为反对佛朗哥而拒绝返回西班牙,这也不是“背叛祖国”。
台湾是一个妻子,因为我从这个岛上的男友变成了丈夫,再变成了父亲,从年轻的讲师到沧桑的老教授,从“新人”到“前任”的写前言。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大约半个世纪前,我从厦门经香港来到台湾。我玩跳棋,跳了三个小岛,在台北定居。虽然我去美国五年了,去香港十年了,但台北仍然是这一生中最长的城市,而高雄则是第二长的城市。我的“两个城市的故事”不在巴黎或伦敦,而是在台北和高雄。
我以台北为家。在城市南部厦门大街上的一个小巷子里,“就像蠕虫回到草丛中,鱼在底部潜水”,我已经休眠了20多年了。我不仅有四个女儿,而且还有23本书。晚年从海外归国时,他在西子湾高雄港住了13年。厦门街113巷是一条深and而又神秘的狭窄小巷,岁月如锅底。相反,西子湾湾被整个寿山山与高雄市隔开,但它向西敞开,拥有广阔的海洋和天空。就集装箱吞吐量而言,高雄被称为世界第三大港口,在我的窗户下面的广阔空间可以捕捉到七海的风浪。在诗人的晚年中,有这样的写书海峡,比老杜的《江夏》还要宽。
不幸失去了母亲,何星又遇到了妻子。这种情况并不完全是隐喻的。在现实生活中,我慈爱的母亲生下了我并抚养了我,在我放手之前,他带领了我三十年,然后由我的好妻子接任。没有这两个坚强的女人,今天怎么会有我?在隐喻层面,大陆和岛屿尤其如此。因此,我心怀感激,写了一首诗《断奶》,并以这三个句子结束:
断奶的母亲仍然是母亲
我很幸运
打破了莱祖和妈祖
虽然海峡宏伟,但它就像一把残酷的蓝刀,将我的生命减半。不管我写多少首怀旧诗,都很难缝合伤口。夫妻俩一直在吵架,被夹在中间的一字一夫感到最难过。我应该是男人的儿子还是丈夫?无论是在大陆,香港,东南亚还是在国际上,我一直被称为“台湾作家”。我当然是台湾作家,从广义上讲我也是台湾人。当然,台湾的不幸,繁荣和耻辱是共享的。但是我也是,我是清晨的中国人:中国的河流,山脉,人民,文化和历史都是我与生俱来的“家庭”,我不能再忍受了,中国的不幸,繁荣,荣誉和丢脸也是我的。无论如何,独特的“胎记”是无法消除的。但是,在今天的台湾,很多时候,任何想成为中国人的人都只是犯了“原罪”。显然他们都是马,但我不得不说,白马不是马。这个矛盾是一个漫长的故事。我只有一个天真的希望:“不要在五十年的政治中放弃五千年的文化。”
香港是一个情人,因为她和我的命运已经十二年了。尽管我们终于分手了,但这并不是因为争执。当我第一次见到她时,我只有21岁,而且我是一个从大陆流亡的学生。一年后,我东去台湾。当我再次遇见她时,我已经中年并成为中文大学的教授,她是一个光辉灿烂的时期。我为她写了很多诗,写了一些更美的文章,这让台湾的朋友们羡慕不已,西行了,我不得不到现场去验证。所以那十一年也是我“后期”创作的全盛时期。此外,我院里的大多数同事都是文渊的知己,门徒中也有很多新才华,这成为了沙田文学的风格。
长期以来,香港一直是国际大都市,也是大邑。东西方,左右方并存不仅有反差,而且南北交通可以赢得城乡地区。的确是混血儿。她的熙熙the的城市使大多数游客眼花,乱,而忽略了她美丽的大海和群山。九龙和香港隔水相望,两岸的灯光早已令人眼花。乱。随着海浪的反射,盛况翻了一番。至于地形,它像半岛一样延伸,像港口一样收缩,像峰峦叠,像岛屿一样散开。随着船只的来回,许多变化使海景变得奇妙而无尽。我看了十年,仍然不贪心。
我一直很幸运能够在香港无限的美好岁月里在沙田教书。我很幸运,美丽的大海和山脉,安静的校园以及自由的学习方式使我得以在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之中登上大陆的后门。幸免的象牙塔专心地写了几本书。因此,我的“台湾作家”实际上离开了“香港时代”。
但是这个恋人一开始并没有一见钟情,甚至有点勤奋。例如,她的广东话口音很难理解。有时候她喜欢写简体字来测试我。如果她得罪了她,她会在左报纸上嘲笑我。所以头几年让她有些痛苦。后来,相识逐渐加深,她发现了自己的真实气质,终于变得快乐起来。不仅可以理解广东话,还可以阅读简体字,甚至连他的美国英语也已更改为保留的英国口音。同时,我对英语世界的兴趣也从美国转移到了英国。香港已经成为我去欧洲的跳板。不仅因为香港人比台湾人来欧洲早得多,而且还因为签证在香港更快,更方便。当内地在1980年代初逐渐开放时,内地作家出国交流,其中大部分是从香港开始的。因此,我遇到了朱光潜,巴金,辛迪和柯玲,并且也开始与流沙河和李元lu进行交流。
许多人看不起香港,认为她只是一个殖民地,并her毁她为文化沙漠。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去世。五天后,举行了葬礼。国旗在香港降半旗。为了向文化领袖致敬,我不记得在其他中国城市也有先例。至少胡同年去世,台北没有。这样的香港可以称为文化沙漠吗?至于近年来针对6月4日和钓鱼台的抗议活动,场面和牺牲都不像是一个柔软的殖民地。
在我将年迈而又不衰老的美好岁月里,欧洲开始成为外遇。我首先练习了欧洲和土耳其。我从纽约起飞,从伦敦进入。我绕了一个大圈。我当时48岁。当我真正踏上巴黎的鹅卵石街道时,它已经五十岁了。我的心情不仅有点“迟到”,而且这个季节也是春节联欢晚会,但这是一次单独的访问。当我老去花都的时候,我不禁感到自己让自己失望了。我记得李清照所说的话:“春天回到陵墓,老将建康城。”
巴黎人对法国艺术的浪漫和温和有一点了解,而眼下的巴黎总是比一般游客所见的丰富。 “以前我只是在印象派绘画中看过巴黎,这是虚幻的和合理的;当我亲眼看到法国时,我怀疑自己是在印象派绘画中的,这是真实而合理的。”这句话的开头。
巴黎不仅是花卉和艺术之都,还是欧洲的首都。整个欧洲当然已经是“晚期”,但它仍然非常“美丽”,也许由于它的迟来性,美丽甚至更可怜。此外,由于文化差异,它们既是暮色又具有不同的风格。例如,伦敦的成熟度仍然很高,而巴黎不仅魅力十足,而且有点闷热。
总体而言,北欧的城市更为典雅,而南欧的城市则更为华丽。新教国家清醒温带,旧国家则懒惰而热情。因此,尽管斯德哥尔摩享有“北方威尼斯”的美誉,但冬天长而夏天短,寒冷的光线倾斜,塔等建筑大多由红色和棕色的方砖制成。大面积的阴郁处,波浪压力低。波浪变少了,蓝色变多了,没有金的美。在如此黑暗的海浪中,南欧的明亮风格是无法想象的:格拉纳达的中世纪“阿尔罕布拉宫”是一种穆斯林宫殿,带有精雕细刻的圆柱和弹簧,即使反复擦拭阿拉丁神灯也是如此。 ,它将不在波罗的海沿岸。
但是话又说回来,无论您陶醉还是清醒,传统的欧洲建筑之美总是会让您充满期待和怀念。无论西欧和南欧,即使东欧小国,无论它们多么脆弱和“落后”,其传统建筑(例如城堡,宫殿和教堂)仍然比现代城市更具吸引力,蓬勃发展。在经历了纳粹灾难的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岁月的沧桑仍然无法摧毁这些暮光之城。一旦维也纳和布达佩斯在多瑙河的映照中,或者在战神的大剑之下,让布拉格的桥躺下。和水平。爱伦坡说得很好:
你女神的恩典把我吸引回了家,
重返希腊不再光荣
罗马逝世的盛况。
如果所有美丽的风景都具有历史回响和文化意义,那不仅令人兴奋,而且使人们徘徊。此外,欧洲文化不仅源远流长,而且多元。 “外遇”的滋味远非美国的单调和肤浅。不管美国有多富裕,我都为在波托马克河边建造卢浮宫感到ham愧,对吗?难怪王尔德想说:“好心的美国人死后,他们都去了巴黎。”
1998年8月在西子湾

 好心情的经典语录
好心情的经典语录 经典成长语录
经典成长语录 问心无愧的经典语录 坦荡做人无愧于心句子
问心无愧的经典语录 坦荡做人无愧于心句子 迎接明天的经典句子 奋斗明天会更好的语句
迎接明天的经典句子 奋斗明天会更好的语句 主君的太阳经典语录
主君的太阳经典语录 盛世嫡妃经典语录
盛世嫡妃经典语录 成功人生规划经典格言
成功人生规划经典格言 2017经典励志格言
2017经典励志格言 墨子经典语录
墨子经典语录 爱神经典语录
爱神经典语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