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一刻,也千秋
一会儿,直到永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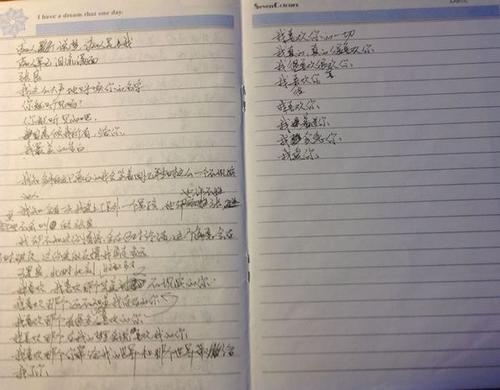
文/史立松
“连霞我的妻子”,看到这四个字,她的整个身体的血液突然凝固,她的思想一片空白,初春的阳光下的温暖,好像突然被一股寒流袭来,消失得无影无踪。
周连霞颤抖地发现刚从一堆旧报纸上随机撕开的航空信封。一堆五颜六色的邮票,圆形,方形和三角形的邮戳,端庄且略带残酷的传统常规字体,在信封的右上角,她终于找到了两只用钢笔画的小蝴蝶。她爱抚着飞过数千座山川的蝴蝶,飞了几十年的寒热,低声说:“绿芙...”有一段时间,她充满了情感,从眼角流下了眼泪多年生病的眼睛。一串串的水滴落下。她拿起咖啡桌上的老花镜,坐在阳台上的旧藤椅上。窗外无花果树枝的影子一次又一次地遍在她的脸上,就像寂静岁月的痕迹。这封信很长,她只能读四个字:“他还活着。”
正如她一直相信的那样,他还活着。
他是她的丈夫徐路福,她已经迷路了35年,没有消息。
那是旧上海最繁荣的时代。在上海,一位著名书法家和画家的小沙龙里,周连霞穿着清醒的旗袍。她修身,美丽,优雅。悲伤使她成为一群时髦的女画家之一。 ,更加风趣。徐路夫被她深深吸引,他的心像新鲜的核桃一样被敲开,清澈的溪流g绕。
徐绿福是上海一位年轻而著名的摄影师。周连霞多才多艺,擅长绘画,书法和诗歌。她与吴庆霞和卢小曼一起被誉为“上海三美女”。她曾在上海西镇女子学校当过国画老师,并为王兴吉范庄卖了扇子画。那时,她刚刚离婚,最后一次婚姻给她带来了创伤。
徐露夫开始疯狂地追捕周连霞,他的每一个毛孔似乎都充满了激情。他每天给她写一封求爱信,每天三封,他会在信封的右上角画两只会飞的蝴蝶。他在信中说:“在孤独的路上,我看到了你最美丽的时刻。”他爱她,无论如何,他不在乎她是否比他大5岁,更不用说她曾经的婚姻历史了。
心灵交流需要真诚的桥梁,爱的诞生只需要通向心灵的道路。爱是一种伤人的武器,也是一种良药。周连霞一度饱受摧残的心因他那炽烈的爱而得到了治愈。他们就像两只飘扬的蝴蝶,在爱的花朵中徘徊。不久,他们在教堂里举行了一场简单的新型婚礼。
结婚后,他带领她走过了上海的各个角落。他以她为模特,并拍了无数照片:在黄浦江边,在钟鼓楼前,在红李子树下,在街道和小巷里,到处都是她的影子。那年,他在《人民生活》杂志上发表了一张她的照片:精致的旗袍,轻盈优美的身材被纱帘遮住了一半,脸庞平静,优雅,精致,嘴角微微浮起。方向迷人,微妙而迷人。他们发表了他为她和她的画作拍摄的照片集,并将它们命名为“电影和画集”,以纪念他们结婚一周年。
美丽的爱,就像一罐醇香的葡萄酒,总是给人灵感和激情。周连霞的创作热情蓬勃发展,她的画在第一届加拿大国际展览会上获得了金牌。她的长篇小说《宋先生的浪漫史》,《美女》和《迷失的珠子》在《万象》中出版,都是痴迷的男人和女人。她写有关感性和无意的故事,但她杰出而又不庸俗,像纯洁的莲花,温柔而优雅;她还带头建立了中国妇女书画学会。同时,徐路夫也步入政治舞台,稳步上升。
上海沦陷后,徐路夫去了重庆。最初认为这只是一小部分,但目前的局势动荡不安。留在“孤岛”上的周连霞在等待时不可避免地会孤单。爱美是女人的天性。她花时间打扮,“每一天,美好的一天”。她本身就是美的胚芽,加上精心的装饰,尽管周连霞是中年人,但她仍然很诱人。她也天生豁达,自由且容易相处,因此受到许多男人的追捧。如果丈夫不在身边,那么麻烦时期的美丽自然是不可或缺的。一段时间以来,上海许多小报都生动生动地散布着她迷人的故事,开玩笑地称她为“连石娘”。她对那些不真实的话笑了,不赞成。
抗日战争胜利后,徐鲁夫被派往台湾接管邮局。这次是春季和秋季的几十年,浅海峡变成了一条银河系,他们无需喜bridge桥就可以穿越。
新中国成立后,周连霞在上海美术学院任高级画家。在海峡的另一边,有一个无法触及的禁地,甚至世界末日也遥不可及。有时,有人会问起她的丈夫,她总是轻声说“早逝”。回头,望向远方,静静地湿透,静静地擦干眼泪。有些人对她的美丽和才华感到不知所措;有些人真诚地想照顾她一生,还有一个重要的人要给她慷慨的生活……她微微一笑,轻轻摇了摇头,拒绝了。她在等他。尽管她的丈夫就像冬天的天空中的晨星,遥远而寒冷,但她无法忘记他。他更像是她生命中的月亮,在安静的夜晚散发出柔和而明亮的光芒。她坚信,有一天,他会突然站在她的面前。
思念在我心中折迭,相思写在纸上。它们是会飞的蝴蝶,她没有理由独自飞翔。她喜欢给双鸭涂上man,向双飞涂上蝴蝶。在她的画作《唐诗意向》中,她题词:“与女儿独处的一刻,一刻,这将是永远。
她的誓言和毅力是“即使是一刻,也永远”。在梦中,仍然是在火车站告别的场景。他从远处走过去,正要握住她的手,但被人群冲走了……醒了,只留下了无限的忧郁:“现在,这只是一个回忆,人们孤独地站在灯的后面,人们寂寞的灯后,有一千个念头,没有梦想。”她还填写了《西江月亮》:“窃窃私语了几次,道路又冷又轻,夜晚仍然很浅;早点回来。睡一会儿,在梦中见到你。提醒您,您不会忘记,星星将孕育光;但是,让两颗心发光,没有光,就没有月亮。”
每天,她都会早睡,希望她的丈夫在梦中见面。自从他成为折断的风筝以来,她一直住在上海,很少去其他地方。她担心有一天他会回来并且找不到门回家。失踪永远不会消失,直到她老了,她在十字路口等着,逆风站立,伸出双手,等着他带领。
等待中,时间是盛开的花朵,但等待中的不是芬芳的蜜汁,而是阵阵风雨的“文化大革命”。她未能逃脱被批评和战斗的命运。她没有写任何人的大人物海报,并且从不公开其他人。她只会在打架时喃喃自语:“我有罪,我有罪……”
在那个疯狂的时代,跳下建筑物的人多于凋谢的花朵,但她无意自杀。 “没有光,就没有月亮”成为犯罪。她被指控“是黑暗的,不是光明的”。她被红卫兵殴打,一只眼睛受伤并致盲。她不仅没有选择死,还要求有人刻两枚图章,一个是在“楚辞”中使用“木休休修”一词,一个是“一目了然”的成语。她心里有强大的力量,正等着他。等待他使她的生活纯净而超脱。
从上海书画院退休后,她独自生活在小巷深处。眼疾越来越严重,但这并不能阻止她有条不紊地组织生活,也不会妨碍她对美的热爱。灰白的头发在头后部扭成一个小发bun,是一件青色的毛衣,再加上一个链扣毛衣,简约而又优雅而沉稳。岁月悄无声息地过去了,他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在他的一生中,他的烙印很少会很轻松,但多年来他已成为一种习惯。写诗,画画,种花,养鱼,与他无关的一切,似乎都与他有关。
终于有一天,他写道。
云开月仙,她的生命在她的晚年恢复了光彩。他从美国回来,带她去探亲,接受治疗。在美国,她治愈了困扰了十多年的眼部疾病。在国外,他们在一起生活了很长时间,使他们的老年变成了明媚美丽的春天。

 很有水平的话
很有水平的话 同事之间感恩的句子
同事之间感恩的句子 关于行善感恩的句子
关于行善感恩的句子 感恩你的出现爱情句子
感恩你的出现爱情句子 关于感恩家乡的句子大全
关于感恩家乡的句子大全 向情人示爱的话
向情人示爱的话 关于爱情甜蜜句子
关于爱情甜蜜句子 年后第一天上班激励语
年后第一天上班激励语 离别不舍又必须走的诗
离别不舍又必须走的诗 晚上江边美景的句子
晚上江边美景的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