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上北大的农村学子
北京大学农村学生录取

文/成梦超
7月25日,云南会泽县崔少阳收到《北京大学录取通知书》。就像休假的每一天一样,他正在帮助外来务工人员的父母在离家大约十英里的一个建筑工地上搅拌砂浆。在收到通知之前,他几次擦了擦汗衫的手。
“在施工现场收到北京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消息在互联网上传播开来,崔少阳开始流行,刚从北京大学毕业的邓凤华也看到了这一消息。他也来自会泽,还是一个农村孩子。晚上很安静。他以正式帐户给弟弟写信:
“入学前必须绑定到建筑工人的象征”“对于您和我来说,味道真是奇怪”。邓凤华已经在北京大学工作了4年,现在是清华大学的研究生。他知道,在这些地方,“岁月平静而美好”,“忘记过去是如此容易”,每个人都“学习摄影,化妆和音乐会”。从内而外,收拾自己”,“建筑工地和建筑工人似乎是另一个世界。”
崔少阳看到了邓凤华的信,并说:“许多影响仍不为人所知。”最近,他被媒体包围,在镜头前害羞地说道,他想“重返山峰,改变山脉”。但是他私下里承认他“不知道如何改变”。
这位年轻人说:“可以考入北京大学。”他仍然相信,努力工作可以改变一切。入读北京大学后,他立即购买了一整套雅思教材,并将其堆放在狭窄的住所中。
邓风华希望崔少阳能意识到,有些事情是勤奋解决的。在信中,他用黑体和粗体写道:“即使在北京大学,我们也是亿万农民工人的镜像。”
2018年8月30日,北京大学本科生注册。
1个
北京大学的外观,崔少阳根本不清楚。他并不健谈,并且喜欢打篮球和读高中。他从来没有走过。从高中到家庭,他必须乘坐40分钟的乡村小巴,然后在山区道路上步行20多分钟。下雨时,泥土会粘在脚上,因此回家时必须擦鞋。
崔少阳在入学是否带父母去北大报到之前苦苦挣扎。钱是问题所在,更重要的是,“来时我无法照顾它,而且我也不想玩。”
邓凤华先是挤了一辆3小时的货车从山上下来,堆放行李,饲料和铁锹,然后从县城乘4小时的公共汽车到昆明。道路几乎是所有深山和山谷,最后是从昆明到北京。这条山路的记忆并不美好:这条路以前曾与乡政府相连,步行回家花了十多英里。冬天,他和他的姐姐背着行李,雨雪打着他们的脸拍打着脸,回到家后,他们常常会因口鼻发麻而变得麻木。
他同级别的农村朋友徐森第一次来北京大学参加自我招募。他在东门找不到食物。父子俩缩在地下室睡觉。北京给人的最深印象是到处都是冰冻和滑倒。后来,两个人去了西单的购物街,一个打零工的父亲对价格无言以对,“你把我带到了错误的地方。”
另一个人曲小伟被父亲送上学了。两人在紫禁城前站了很长时间。他们觉得门票太贵了,没进去。他父亲随后去平谷打工,赚了一些旅费。过了一会儿,女孩从父亲那里收到一条消息:“平谷还不错,它类似于我们的家乡。”
屈晓薇和她的室友偶尔一起逛街。一些女孩每天下午在雅诗兰黛和兰蔻上花费两到三千元人民币。她觉得化妆伤害了她的皮肤。业余时间,她主要在图书馆工作以帮助学生。北京大学的资助系统足以使学生完成学习而不必花一分钱。她的“敏感”时刻在别处:例如,她不懂Word或Excel,几乎死于计算机课。或是在江苏城市长大的室友为她选择课程,并选择“最容易获得高分”。 “孟子论语”,期末考试是默默地写“孟子”,她差点没通过,她的室友震惊又内地说道:“对不起,我想你会背诵。我们都背诵。”
邓凤华和许多农村孩子都被英语困扰。在考试的前两年中,普通人得分超过90分,而他的最高成绩是80分。 “通常做演示时,它们都是即兴创作。我纪念,甚至阅读它,我的手掌仍在出汗。”在高三之前,他修过哲学双学位课程,许多新生都用英语直接交流。他整夜准备,无法跟上,仍然“非常紧张,感到难受”。
徐森学习力学。用他的话说,当他的同学从教授的父母那里得知广义相对论时,他还在乡村学校的图书馆里,读着1980年代的《十万个为什么》。 “科学也需要直觉,感情是隐藏起来的。”
这种差异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徐森入学时加入了很多俱乐部,例如国际象棋俱乐部,但是很难融入这些圈子。他认为自己喜欢下棋并且水平很高,但是俱乐部真正的核心成员已经处于比赛水平。他通常会交换国际象棋记录,并且他根本不懂很多专业术语,而且不会说话。
上海交通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自招生与农村特殊应聘者的适应能力存在显着差异:超过一半的自招生具有较高的学校适应水平,但只有约10%的农村特殊应聘者可以适应。达到相同的水平。
今年1月,北京大学学生资助中心向2017年资助的学生发放了调查表。在返回的135份问卷中,有62%的学生认为他们的学业基础差,而一半的学生则认为他们缺乏自信并且不善于社交。 68%的人没有明确的学业计划。
崔少阳也有些担心。他在高中时的主要烦恼是他无法社交,与同学和老师交谈,内心充满言语,但他无法说出来。另一方不知不觉离开了,他感到非常不自在。最近,有数十个电话要求他进行采访和资助。他回答了每个人,然后礼貌地拒绝了他,但他经常被迫无语。
邓凤华参加了基金会的交流活动,发现那里的大多数学生胆小,不敢主动讲话。有人在交流时cho之以鼻,说家庭不容易,很难适应学校,“自信,敬业精神和强大的现场控制能力”“北京大学与众不同,一切都像我的故乡。
他记得光华管理学院的一位乡村朋友。两人刚到北京大学时,便一起去中关村买了台电脑。对方高兴地笑了,说他们必须做很多事情。当他们在大二的时候见面时,对方的体重很大,成绩很差;他们高三毕业的时候,他们一起吃晚饭,对方痛苦地笑了。 ,“滑到尽头”,他的许多同学都出国了,他回到了家乡“找工作,入不敷出”
邓凤华还觉得自己和其他学生之间的区别是一件坏事。但是请仔细考虑:我5岁那年,我被塞进了姐姐的教室,每天来回走十多公里,坐在教室后面听课;我10岁那年,我住在学校里,用40多个同学的水盆洗了脸。在北京大学,我父亲笑着说:“看看你家门前的山。你能通过考试吗?”
但是当他到达北京大学时,即使他不想这么做,外界也会告诉他,两者之间还是有差距的。在大一的时候,辅导员找到了他,并恳切地建议他可以打网球,“这样他可以更好地与同学融为一体”。
邓风华说,这是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确与他们不同。
2017年9月8日,北京大学举行了2017年开幕典礼。
2
与早上3点施肥和早上6点施砖相比,崔少阳认为学习是“最不累的事情”。
崔少阳中学最喜欢“平凡的世界”。他曾经瞄准了终生驻扎在农村的孙少安,因为“他对家人和警卫负责”。他的两个父母都通过兼职赚钱,但仍然负债累累。为了弥补他去北京大学的旅行,他的父亲今年夏天因怕雨而努力工作。崔少阳除了每天在建筑工地上工作超过10个小时外,还坚信读书也可以“保护家庭”。
他的家几乎是崎rough不平的,卧室里没有桌子,各种各样的建筑材料散落着。客厅里的老式电视架在两块空心砖上。父亲cho咽,说在家里不容易。孩子们上学,有时还买了火腿肠来填补他们的饥饿感,但他骗他吃得很好,包括土豆,肉末和白菜。 。崔少阳也在他旁边擦干眼泪,说他父亲三年前有肾结石。他认为那是绝症。他计划最后一次见到他。一顿丰盛的饭后,他放弃了治疗,但出人意料地忍受了上厕所和排石的痛苦。 。他承认,知道了这一点,他“就有学习的动力”。
邓凤华小时候曾帮助父亲收烟,他在田野里忙得不可开交。将其弄碎后,将其带回家进行熏蒸,然后需要点燃烟草下面的炉子。烟雾散落,人们睁不开眼睛,身体被烟油覆盖,衣服会粘在一起。他心想,通常要一直呆到凌晨两三点,长大后不要继续种植这种东西。
邓凤华的父亲只希望他的孩子离开那间破旧的房子,在雨天破烂不堪,随时可能倒塌。他曾经认为,给儿子最好的出路是读书,读初中老师到县城,赚稳定的收入,并成为这个城市的公民。现在,我的儿子拥有美好的未来,他的愿望上升了-成为高中或大学老师会更加稳定。
自邓凤华出生以来,这个想法就没有改变。邓神父种了四到五英亩的烟草,养了猪,还用铁丝在闲散的地方挖。
后来,他的女儿上大学,儿子上高中。他要求他在隔壁村庄的朋友在几英亩的荒地上种玉米。土地裸露在山顶上,脚下是云南和贵州交界处的大峡谷。通常是安静的,像在空中一样。
“我告诉他,他必须参加考试。我将再次在现场和我一起哭。”
邓风华后来意识到,在自己的环境中,几乎每个人都认为学习的目的是远离原始环境。他的高中老师很欣赏他,并拍拍他的肩膀说:“我想被北京大学录取。如果你被北京大学录取,你将用半只脚进入上流社会。”当时,他非常感动。
在他站在盐源之前,他还茫然地问:“上层阶级是什么?”
过去的经验不能回答这个问题。例如,屈小薇甚至都不知道为什么要被北京大学录取。同一个村庄的某个人以前曾被北京大学录取,她的父母为她定了目标。在第一次高考中,她被南方一所著名大学录取,但是她没有钱在家里盖房子,负担不起学费。高分考生回国学习将获得3万元奖金。她被迫学习了一年,发呆地来到了北京大学。
同样来自云南山区的凌雄也以一种含糊的方式去了北京大学。他是理科学生。结果公布后,他最喜欢的专业是北航飞机或同济土木工程系。但是他们的高中从来没有北京大学的学生。校长要他说话,老师也恳求他“赶”。因此,他填写了提前批,然后到北京大学寻找一种不受欢迎的少数民族语言。
“我以前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这个国家。”他将注意力转向课外生活,并参加了许多俱乐部。我认为这更接近“每个人都想要的生活”。
“蓝图很好。但是它根本不适合您。”凌雄的大一和大二学生严重失眠,倍加焦虑。
他仍在忙着做生意来赚钱。他的父母是在建筑工地上搬运钢筋的工人,他想致富。但是他发现,他努力工作的一些创业思想要么被消息灵通的同学指出是不可靠的,要么提醒人们已经存在类似的项目。即使他们遇到一些可以赚钱的好项目,也有一些学生可以投资5万元,但他却没有这么多闲钱。
最后,他在大学的第一笔生意以失败告终-他借了4万元人民币买了茶,他想将其卖给学校和附近餐馆组织的会议。现在所有这些茶叶都堆放在家里了,他不仅没有赚钱,还欠了债。他的父母帮助他偿还了部分债务。
邓风华说,过去,他信奉成功的研究,并认为“不成功就意味着不努力”,但后来,他发现似乎存在着比努力更强大的力量。在这种力量的作用下,他感到茫然。在他来之前,他只有模糊的计划,例如“出国”和“做大事”。后来,这些离他越来越远。
崔少阳认为,艰苦的工作一定会有所收获。他认为自己的好成绩使今年夏天的家庭笑容增加。上高中时,他也曾设想过在一个大城市里工作,但他的想象力有限,他想不起白领的生活。相对确定的是,只有毕业后才能为家庭赚钱。
邓风华的思想正在慢慢改变。一个在家乡早婚的伴侣通过喝农药自杀了。邓风华无视家人的阻挠,去坟墓敬拜,不知道为什么一个年轻人死了。
后来,他遇到了一个儿时的同学,他已经是家乡的农民工。另一方告诉他,他已经在外面工作了三年,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并没有节省很多钱。现在工厂已经机械化,机器人取代了人们,工资降低了,他最近失业了。同学认真地问邓风华:“你学得好,我小时候就问过你问题;现在你在北京大学,你能告诉我怎么做吗?”
邓风华想了很久,但没有给出答案。
3
在北京大学,有许多外部力量来吸引这些农村儿童。
北京大学学生资助中心主任陈正伟告诉《中国青年报》和《中国青年在线》记者,北京大学提供的各种资助可以满足学校学生的基本需求。目前,它将提供进一步的“非金融支持”以满足他们的发展需要。
在陈正伟看来,差距是客观存在的,而学校所能做的就是将其最小化。例如,近年来,北京大学为受资助的学生设立了特殊的国内外考察团;它还将邀请一些学校负责人,教授和知名校友与这些学生交流,聊天和就餐。
在西南山区长大的阎泽,在资助中心的帮助下,第一次去了福建,第一次去了日本。他还成为了学生服务团队中学生服务团队的骨干。缺乏英语口语能力的资助学生将与每周的晚餐相匹配,以使学生有机会练习英语口语。
去年,在资助中心的“燕子花园牵手”项目下,她与一个家庭背景相似的女学生进行了比赛,带她去吃饭,在未名湖附近散步,并给了女学生一个礼物。学习建议。从刚开始上学时胆怯而害羞的她逐渐变得开朗。
北京大学的生活总是有出路。徐森性格内向,不能与其他人玩耍,因此沉浸于学习中,因为“做物理不需要社交。”大二那年,他到海外留学机构学习了出国费用,发现仅仅写申请文件就要花费3万元,再加上出国后的考试培训和巨额费用,他“卖掉了房子,可以不明白。”最后,他未能以硕士水平出国留学。取而代之的是,他留在这所学校读研究生,计划将他送到博士后。
屈小威也退了一步。她有机会留在这所学校读研究生,但一年的学费超过2万元,她去了另一所“双头等”大学,这不仅降低了学费,而且还相当可观的奖学金她的父亲说服了她留在北京大学。她说她“不想再学习了”,在电话的另一端cho住了父亲。
“当我们做出选择时,很难忽略成本,而要考虑成本效益。”严泽说。
广州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谢爱蕾对来自4 985所和211所平台大学的2000名农村大学生进行了一项调查,发现农村孩子也可以在精英大学中实现自立,这通常是通过用他们的精力去学习并放弃部分社会生活。
“北京大学的生活实际上非常舒适,很容易忘记困境。”邓风华这句话理解为,大多数人都在思考如何在裂缝中实现自己,而不是缩小差距。
他开始看他长大的地方。他回到山上接受采访,发现许多孩子没有信心。一些父母觉得孩子上大学是不切实际的,更不用说“养一个孩子要花十万元,如果将来找不到好工作,他们会付钱的。”关于从深山进入北京大学的经历,即使涉案人员就在他们面前,许多人的眼神也暴露了他们的怀疑。他熟悉这种感觉,在高中时遇到了很多反对派。爷爷打电话给父亲,说:“修房子比读书好。”
“即使是现在,进入一所重点大学也是很小的可能性。”邓风华反映,虽然家里很穷,但父亲很重视教育。但是在附近的村庄和城镇中,一些家庭仍然相信“穷人最终将变成穷人,政府将对他们进行妥善的管理”。他们指望政府提供资金支持他们,并劝阻他们的孩子学习。
他认为,许多农村儿童来到北京大学,一方面,他们饱受贫困困扰,另一方面,他们拼命逃避和淡化这一限制。有些人开始相信“社会达尔文主义”,并感到自己足够好或勤奋。但是在他看来,正如他从未读过书的母亲所说,他可能只是“幸运地在祖先的坟墓上抽烟”。
在他家,我姐姐在学校还不错。在小学的最后一年,县体育学校招收了体育学生。乡村小学的代课老师以为他们正在招收文化班的顶尖学生,于是他们派了姐姐,包括学校的前三名。
体育学校没有墙。每天有5个文化课,学生每天都会找到一个跑步的坡道。我姐姐跑了半年才脚肿了。没有人负责班级,因此当在二楼扔下1元钱时,一些摊贩把b扔进了窗户。父亲想把女儿转移到另一所学校,但他缺钱,他不愿支付体育学校的补贴。
农村的艰难生活完全改变了兄弟姐妹的生活轨迹。邓凤华是幸运的人,去了北京大学。我姐姐第一年获得了林业专业的良好学士学位,但是农村信息被封锁了,我在接到通知后才意识到学费昂贵,每年超过一万元。为了省钱给她的兄弟,家人要求她辍学。在设置了一个小摊位几个月后,她“心里空了”,她在重复学业后被当地的师范大学录取。
即使在今天,在邓凤华的村庄里,每年仍有两到三名大学毕业生,而另外20或30名仍然选择工作。
在北京大学的一些教室里,一些老师说北京大学的人应该是“完美主义者”。他们去爬山,滑雪,骑马和“过上最美好的生活”。乡村似乎不存在。但是,邓凤华也很幸运北京大学是包罗万象的。许多教授将在课堂上讲话,并希望学生注意农业,农村地区和农民的问题。一位老师告诉他们,这首歌“ In the Spring”最初表达了愤怒的底气和困难,但很容易被“自我奋斗”的表达所取代。
邓凤华逐渐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在纪录片家庭作业中,有一群人在拍摄关于食物的精美影片。他去看了电影《孤独的管家》,记录了学生们凌晨4点睡觉,管家独自在黑暗的走廊上扫地。全班同学都认可并获得高分。他开始关注农村地区和工人的问题,阅读了大量的学术材料,他的同学也很感兴趣,并经常交换意见。
“这所学校有很多可能性。”凌雄第二次创业,并选择返回家乡在农村开设补习班,教孩子们数学和英语。这次他不仅获得了一些财富,而且得到了人们的感激。在一个月的时间里,他看着孩子们笑着嬉戏,看到他们掌握了几乎不懂的拼音和乘法,并且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进步了。只是想赚钱。
4
凌雄偶尔在北京做家教。他看到北京的父母付给孩子一小时零一两百元的课费,以培养孩子的课外技能。他不由自主地想起了自己的童年:小学老师是一名老年代课老师,老人让学生在上课时自己学习,然后在操场上放一张桌子喝酒,然后脸红了回来。宣布下课的结束。
在村子里,除了他,他这个年龄的人都没有获得学士学位。三分之二的年轻人初中毕业并从事非全日制工作,其中许多人已经有了孩子。他考虑了一下,觉得自己主要依靠的是才华。
邓凤华到偏远山区调查。他去南部山区拍了纪录片,记录了一个上学的8岁女孩。
他还去了东莞的一家化工厂工作,看着工人不戴手套就将手放在化学试剂中工作,皮肤被腐蚀到干燥。一名农民工告诉他,他回到家乡时不知道该怎么办,也买不起东莞的房子。
在学校里,他发现长得和父母相似的学校工作人员住在学生公寓的地下室。他陪同阿姨在自助餐厅里跳了广场舞,以了解他们的生活。
当然,他想到了自己的过去。家里只有2米高的土坯房阴冷潮湿,黄色的灯泡使墙上的裂缝更加明显。猪圈吸引的苍蝇肆意地绕着房子飞来。他在县城读书,食堂里的阿姨为他感到难过,并给了他尽可能多的肉。他又黑又瘦,留着胡须。
现在他远离云南的紫外线,已经变白了。他觉得他的一些同学正在脱离原始环境。他与一位父亲是建筑工人的朋友谈论了农民工的经历。好好生活,考虑这些。
南京大学的学者对江苏省两所大学的近200名农村学生进行了调查,发现其中近一半的学生表示“非常愿意”或“愿意”成为城市居民,而这一比例仅为15%。坚持农村身份。尽管73.5%的学生认为“自从您在城市以来,您就必须适应城市生活”,但只有7.3%的学生认为他们是“城市人”。
邓凤华的父亲觉得儿子的想法有点奇怪,应该当老师。 “在小学时,老师认为他还太小,无法接受他,所以我摆好饭桌并强迫他们接受。现在在大城市,我们已经不可能了。”邓父亲叹了口气,担心儿子的心跳加快。像女儿一样,最好当九到五岁的老师。
但是邓风华却不这么认为。他希望农村学生能够意识到原来的家庭并不需要逃跑,而是行动的源头。他说,尽管他对某些问题的看法可能与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有很大不同,但他不再感到自卑。但是他清楚地知道这两种理解方法是平等的,并且他可以为他们提供不同的经验并赢得他们的尊重。
5
大四时,邓凤华带了几名新生,参观了云南农村。在那儿,大一学生一直笑着,谈论综艺节目和偶像剧。在他们到达山村小学之前,全班都是留守儿童。大学生们问孩子们在过去一周里对他们感到高兴吗,但没人回答。一个月了,他们仍然想不起来。一年来,仍然保持沉默。最后,一些学生颤抖着说,爷爷死了,爸爸已经三年没有回来了。
在回程的火车上,话题发生了变化。这批新生开始认真考虑农民工的问题,他们的偶像被遗忘了。
无论他们是城市还是农村的孩子,四年的大学都可能是他们彼此深入接触的第一个机会。乡村儿童也有可能取得令人欣喜的变化,例如,颜泽,她感到自己变得更加自信,细心和负责任,得到了很多认可,并学会了与他人相处和沟通行使。 。
“我走在父母从未走过的道路上。这就是我所尝试的一切。”严泽会觉得在来北京大学之前,他心胸狭窄,只想“过上好日子”。但是,当我看到周围的一些学生时,我意识到自己对某件事感兴趣,或者对团队的关心才是持久的动力。
邓凤华的家庭也正在发生变化。他们的家庭曾经是该村的废墟居民,但现在我姐姐已经成为一名老师,建造了一些新的砖房,买了电视,并安装了太阳能。他被北京大学录取,使这个家庭成为该村最受欢迎的家庭。亲戚和朋友开始在假期里送孩子们去,让他们与兄弟姐妹聊天和学习。一些原本希望孩子辍学工作的父母,看到了家庭的变化,并逐渐改变了主意。
另一面,原生家庭带来的身份也长久地影响着这群学生。曲小薇今年毕业,没回家,直接去了研究生的学校继续学习,主要为了省下回家的路费。她认为硕士毕业后去昆明工作,是适合家境的最优解。
北京大学就业指导服务中心统计毕业生去向,也发现农村学生的流向特点鲜明:他们出国深造的比例大大低于全校平均水平,更加稳定、有较高的职业声望及较高保障性的国企和事业单位则是首选。
曲小薇坚信,原生家庭的影响不会抹除。她希望以后赚钱,给老家的小学捐一个图书馆,再给村里装上路灯。凌雄则已然工作,身为选调生前往基层。在家乡开办辅导班的经历让他觉得,能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是一件令人快乐的事。
类似的烙印也留在了崔少扬身上。他就要开学了,资助都已到位。可他最挂念父亲的身体——父亲最近总感觉肚子里“有气泡”,很担心,却还是不肯去医院检查。这成了崔少扬的心病。他也还清楚记得贫困的滋味:自己600度近视,父亲曾省下治疗肾结石的钱给他买了眼镜,他却不慎摔碎了——他痛恨自己,从此再没配过眼镜,不得不凑近看很多东西。
自认“融入”还不错的严泽也清晰地记得贫穷带来的不适感:小时候,她沉默地听朋友讨论麦当劳、肯德基,插不上话;再长大些,同学们问她牙不整齐,为什么不去矫正,她哑口无言;到了北大,开学后会有同学说自己暑假在洛杉矶,或者寒假在旧金山吃到了很棒的甜品,但现在,自信的她放下了这些。
邓风华已经克服了落差感,他在乎深山里的老家,也想改变它。家里只有铺太阳能的屋顶信号好——假期,他抱着电脑坐在屋顶上学习。夜深,绵延的山漆黑,万籁俱寂,头顶的星辉洒满夜空,电脑荧屏闪着光。(文中北京大学学生均为化名)
原文刊载于《中国青年报》2018年09月05日12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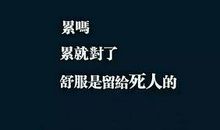 青少年励志句子
青少年励志句子 励志人生哲理的句子
励志人生哲理的句子 关于人生处事的励志语句
关于人生处事的励志语句 英语励志谚语带翻译
英语励志谚语带翻译 励志女人大气的句子
励志女人大气的句子 励志微信名字大全男
励志微信名字大全男 个性签名励志奋斗简单 励志个性签名简短霸气
个性签名励志奋斗简单 励志个性签名简短霸气 好听的励志句子简短
好听的励志句子简短 激励一生励志语录
激励一生励志语录 出去工作的励志句子
出去工作的励志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