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少功:红花爹爹
韩少功:花爸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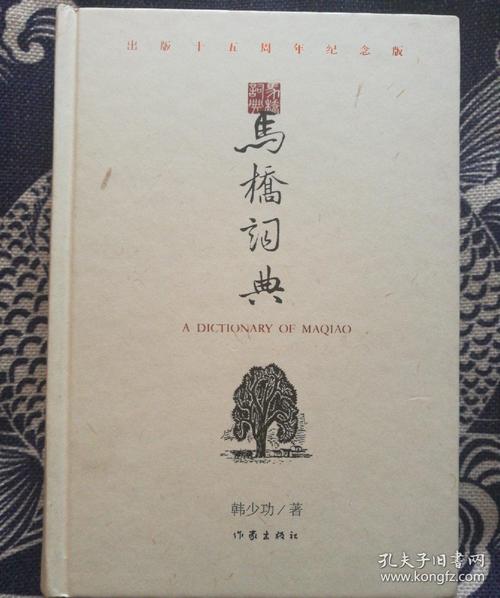
罗布是马桥的移民。土地改革之前,他是长期工,后来担任村长几年,被认为是马桥的元老。有人多次向他建议,但他一一拒绝。他一生都是单身,自己一个人吃饱,整个家庭都不饿。独自工作使整个家庭汗流sweat背。人们有时称他为“红色花朵之父”,红色花朵表示处女身。
后来人们发现他不接受亲戚是因为他没有钱,而是因为他天生就是疏远和惧怕女人,所以当他遇到女人时,他会尽力避免女人。不可能在有很多女性的地方找到他。他的鼻子缠绵而又怪异,他总是闻到女人的恶臭。他认为发生恶臭的唯一原因是要掩盖女性的恶臭。尤其是在春天,尤其是对三十多岁的女性来说,身上散发出的恶臭总是动荡不安,散发着丝丝丝瓜的臭味,漂浮了一百步之遥,鼻子碰到头骨时头晕目眩。保持这种气味一会儿,甚至会杀死他。他一定变黄了,额头上流汗,甚至呕吐。
他还认为,正是这种腥臭味使他的水果变质了。他的房子后面有两棵桃树。每年的花开得很茂盛,但结果却很少。即使悬挂,它们也会腐烂。有人说这棵树病了。他摇了摇头,说那些小偷女人一年要疯了几轮,我要生病了,树可以站立。
他指的是靠近茶园的两棵桃树。每年,妇女都会去那里采茶并大笑。桃子不烂是很奇怪的。
有人不太相信他的话,而是想尝试一下他的鼻子是否真的不同于别人,或者他是否真的很排斥。有一次,他在工作中偷了衣服,然后把它们交给女士们坐下,然后回到原来的位置。将来他会发生什么。
人们惊讶地发现,当他洗衣服时,鼻子两次缩了一下,立即下沉了脸。 “你做了什么,你做了什么,哪一个摸了我的衣服?”
在场的人假装不认识,互相看了一眼。
“我生气了吗?对不起你吗?你想这样伤害我吗?”他用哭泣的脸着脚,非常生气。
窃贼惊恐地逃跑了。
罗布丢下衣服,疯狂地回家。在审查了和平之后,他把衣服拿到池塘里洗了,然后送给了老村长。然而,在随后的日子里,这位老村长从未见过这件衣服,据说他仍然用火烧了它。
人们再也不敢和他开这种玩笑了。邀请他吃饭,桌子上一定不能有女性客人,附近也不能干任何女性的衣服和裤子。在安排他上班时,他还必须注意不要将妻子带到他身边。最初的意思是让他跟随公社的拖拉机在县里购买棉花种子。他去了那里两天。他回来说,他在路上走路时突然腿痛,不得不走路,这很费时间。后来,村民们在公社里遇到了拖拉机驾驶师傅,但才意识到他确实赶上了拖拉机。只是因为车上有几个妻子在搭便车,他拒绝上去,而是宁愿自己走。这也难怪有人。
他走得很慢。他从县里回到马桥,整天走了三十英里。不仅如此,他做任何事情都很缓慢,而且他并不渴望。看来他知道以后有日子,以后又有日子。如果您不需要尹时的饭,就必须在尹时。年轻的几代人喜欢和他一起工作,他们的日子可以更加轻松和悠闲。年轻的一代跟随他到田子岭建造了跨山的渡槽。太冷了,地面上覆盖着冰壳,所有人的脚都用稻草绳包裹着。他们仍然一步一步滑落,跌倒和欢笑的声音接连传来。每个人都低着头来到施工现场。看到没有一个干部在这里,罗布是唯一有话要说的人,所以他们恳求他同意等待,至少要等到太阳出来融化冰才开始工作。罗布困倦地抓着烟袋里的烟草:“谁说不?这么冷的一天把所有人都从床上拖了下来。你应该把主人或母亲埋葬?”尽管他的话不太清楚,但我理解其中的意思。每个人都开心地走了,每个人都在寻找避风的地方,以进行热身。罗布不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垃圾,and下燃着一堆烟花,这使一些人出生在那里并拥挤。
“恐怕我需要提两个篮子的木炭?恐怕我需要设置几个炉子?咳嗽的初衷是,阴和阳的两个开口线掉了,人们跳了起来。我不知道他拿着一根竹竿来测量地球,它从哪里来。
罗布的眼皮上仍然排满粪便,他慢慢说:“道路不稳定,那负担是什么?你没看见吗?那条天狗不在路上。”
是的,人们纷纷效仿。
“要得到!”原来的意思再次嘲笑着:“我在这里请你睡觉。党员带头睡觉,民兵带头睡觉,贫穷而中低等的农民克服了睡觉的困难。你必须睡觉既要有现象,又要有睡眠。知道要睡什么。对吗?”
他还使用了哲学,例如刚刚学到的现象的本质。讲话后,他脱下了Zoro并系好了袖口。他吐在他的手掌上,拿起一块石砖,走到渡槽的尽头。他在这方面也很擅长。在场的人们感到尴尬,干watch地看着他们,看到其他人移动了,不情愿地走出了柔和的角落,顽强地三三两两地打了冷风。
罗布很镇定,抽完最后一口烟后,他也发牢骚,抬起石砖,跟上了当初的意思。这时发生了意外的事情。他只是走到渡槽上,原来的含义在他面前尖叫,身体摇晃,两只脚根本无法稳定。他在水槽的光滑表面上移动,他将要捐献边缘,他将要滑入水中。寒冷在上升的山谷。人们的心突然出现。 Rob在清楚地看到险恶的局势之前,已经眼神敏锐,尖叫着甩开肩膀上的石砖,然后向前冲去,只抓住一只脚就没有抓住他面前的身影。
幸运的是,罗伯(Rob)的脚用钢头钩在了渡槽上,他的身体被冰压着,被沉没的本意拖到了渡槽的边缘并停了下来。
根本听不见最初的呼唤-它被山谷的气流打扰了,就像几只蚊子从山谷的底部来了一样。
“你,说,什么,什么?”罗布只看见了另一只脚。
“拉我,快点……”
“别担心,” Rob气喘吁吁。 “您已经很好地学习了哲学。您认为这种天气是一种现象吗?还是本质?”
“赶快……”
“它太快了,很酷而且很容易说话。”
“妈妈...”
一些年轻人走近,拉紧绳子,伸出双手,并小心地救出了悬挂在渡槽下的秘书。
最初的含义出现后,red()有了一张脸,不再傲慢自大,再也没有哲学,有人不得不抱着他走下水道,然后一步步走。他回到村子里砍了几斤肉,邀请罗布喝酒,感谢他的救命恩典。
从那时起,除了罗伯(Rob)以外,本义就可以责骂马桥的任何人。我本来会喝些好酒,我还会提到罗布的小屋,并请罗布喝一杯。有人说铁祥在三天后与本义发生争执,而本义总是被罗布的地方浸透了,这就是原因之一。他们不仅在喝酒,不仅在说白话,而且还在做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例如一起洗澡,一起躲在蚊帐里,床板吱吱作响,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即使是同一个锅里的兄弟也不能睡在床上,对吗?曾经有人去罗布家后的花园里偷竹笋,然后顺便从窗户的纸孔里往里看。他们感到惊讶:他们固执吗?
这是指男人之间不认真的事情。
马桥人对这种事情并不在意。张家坊也有做这种事情的人。不足为奇的是,附近的乡村象中有一些红花父亲和叔叔红花。此外,白天看到袁一的愤怒在脸上。没有人敢问,也没有办法证明这一点。

 好心情的经典语录
好心情的经典语录 经典成长语录
经典成长语录 问心无愧的经典语录 坦荡做人无愧于心句子
问心无愧的经典语录 坦荡做人无愧于心句子 迎接明天的经典句子 奋斗明天会更好的语句
迎接明天的经典句子 奋斗明天会更好的语句 主君的太阳经典语录
主君的太阳经典语录 盛世嫡妃经典语录
盛世嫡妃经典语录 成功人生规划经典格言
成功人生规划经典格言 2017经典励志格言
2017经典励志格言 墨子经典语录
墨子经典语录 爱神经典语录
爱神经典语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