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事儿发生在协和医院,读后想哭!
这发生在协和医院。我想看完后哭!

文/张瑜
在白天的病房检查中,一名孕妇坚持剖腹产。确实没有医学适应症。腹部的孩子可能不大,骨盆正常。徐教授说,还没有到需要手术的地步,所以让我们先生一下孩子。
孕妇的爱人被困在病房的门口,大喊大叫,为什么我们没有割伤,如果不能出生,就没有必要吗?
“我们不愿意尝试。如果有人使我的妻子遭受第二次犯罪,我将永远不会以她结束。”
那天,徐教授不在值班。她在听到家人在外面大喊的时候说,这位孕妇可能有点麻烦。出生时遇到任何麻烦,请给我打电话。
同一天,孕妇实际上正在分娩,分娩过程进展顺利。但是,在我们常规的胎儿心率监测过程中,我们发现胎儿心率经常减速。我们正在积极地为手术做准备,打电话给徐教授,与家人谈话并签字,家人生气,一边签字,一边诅咒说,如果孩子有三长两短,请期待。
徐教授到达病房后,他也同意我们的观点,希望尽快通过剖宫产帮助孩子摆脱危险。
有什么危险?此刻,生下她的母亲的肚子很危险。分娩是人和自然对胎儿的最后考验,也可以称为十月妊娠的最后自然选择。
每次子宫收缩都会挤压胎儿,挤压出产道,挤压到这个色彩斑outside的外部世界,同时挤压胎儿的胎儿肺中的水,这样,每个子宫中的肺泡在出生。打开以保护孩子的呼吸。
另外,这种挤压还可以帮助婴儿的皮肤在出生后建立触觉和感觉,而且人类还没有充分发现许多好处;这似乎很强大,但与此同时,这种挤压也是对胎儿的最后一件事。考试。
胎儿的血液来自胎盘,而胎盘的血液则来自双侧子宫动脉。进入子宫后,子宫动脉呈螺旋形,就像席梦思的泉水一样,散布在子宫肌层中。
每当子宫收缩时,子宫的肌肉层就会极度收缩。此时,所有的螺旋状子宫动脉都被压缩和干riv。没有血液,就没有氧气。每次子宫收缩,胎儿就相对短缺。在氧气状态下,只有当子宫松弛并且新鲜血液流回子宫动脉时,胎儿才能重新获得血液和氧气。
经过多年的蛙泳,我突然有了学习自由泳的想法。刚开始时,我的基本动作很好,但我无法改变呼吸,仅将头塞入水中就可以游出约十米。教练在岸上大喊,张瑜,你知道为什么你不能前进吗?我回来了,缺氧。他大喊大叫,然后您就不要急着喘口气。我整个早上教了你什么?
分娩过程中的婴儿就像水上马拉松运动员。为了确保他能够到达胜利的另一端,他需要持续通风。这种通气取决于子宫的张力和松弛。
但是,如果子宫收缩过于频繁,或者胎儿耐受缺氧的能力下降,则可能会出现问题。不能忍受缺氧,生一个不哭的婴儿,这是普通人都知道的窒息。这时,如果您想象着像巨大的非洲大草原那样的产房,那么一个没有哭泣就出生的孩子就像一只羚羊,无法立即与母亲站起来奔跑。它无法逃脱狮子,豹子和狼的血,必将成为猎物。
在旧社会中,孩子是在家里的the牙上出生的,没有医生,没有剖腹产,只有助产士,还有一把在火上灼热的剪刀。在向子洛陀,助产士大声喊道,说,向子,你的妻子在“倒挂”,没人能做到。乌努死于难产。小时候,我很清楚地记得这句话,但是我不知道我躺着是什么。后来我成为了妇产科医生。据我分析,胡努可能死于“无视性”。胎儿的头朝下是最正常的胎儿姿势,而臀部的下垂也对分娩有好处,但是如果胎儿在子宫内,则没有剖腹产,并且胎儿不能通过特殊的方式变成头部或臀位技术。最后,子宫将被孩子打碎,仍然死亡,母亲和孩子将一起去黄泉。
但是现在这是一个新社会。这不是非洲大草原,而是人类的文明社会。我们不允许每个婴儿都有问题,也不允许每个婴儿都被选中或淘汰。
但是,当特定的产前检查是一名正常的孕妇时,她高兴地抚摸着大肚子,面带微笑地站在你面前,问医生,我可以自己分娩吗?怎么回答她。
应该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能自己生子。尽管中国进行了社会改革和开放,但它经历了几十年来欧洲旅行数百年的道路。有些地方采取了太多步骤,有些事情可能已经出现。倒退。但是,中国人仍然是中国人,中国妇女或中国妇女。过去,他们能够在旧社会中以the为生。在新社会中,应该说,在医生的帮助下,他们将能够更好地生育。
但是,现实情况是,在分娩至分娩的十几个小时中,总是会有一小部分孕妇有问题。例如,如果原发性子宫收缩无力,没有明确的原因,子宫工作不正常,收缩频率缓慢,收缩强度小,分娩过程缓慢,孩子可以忍受低氧。很久。宫殿里会有尴尬,出生时会窒息而死。
或者,某些婴儿在怀孕初期结合精子和卵子,体内的染色体或基因确定她是一个弱小的婴儿。她的脑细胞,肝细胞和肾细胞都可能少于正常儿童。胎儿的出生体重很小,胎盘也很小。普通人所说的是先天性机能不全,这种胎儿耐受缺氧的能力也很差。
这些孕妇如果在试验的基础上分娩,势必会遭受第二次犯罪,即再次分娩,痛苦,再次解剖并得到一把刀。
如何判断和发现这小部分孕妇可以防止她们遭受第二次犯罪并保护稍弱的婴儿安全地走向世界?答案是,没有办法。
使用当前的检查技术和方法,无法提前知道。作为医生,所有孕妇都能接受剖宫产吗?而且,手术也有手术的风险。我们只能让孕妇尝试分娩。当您有孩子时,您可以边走边看。他们大多数人可以自己生。没有著名的协和教授敢于对尚未生育的孕妇说,如果可以生育,就绝对可以生育。尽管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以这种方式鼓励孕妇,因为只有在孕妇有信心和决心要分娩时,她的大脑才会动员她的整个身体,成为和谐的,具有前瞻性的机车,并体验这座小镇。痛苦,让新生命诞生,这是积极的反馈。
我们可以做的是密切注意分娩的进展,通过医学干预或使用药物加强宫缩,或人为地打破宫缩,及时发现并尽快发现有问题的少数孕妇。刺激子宫收缩的水,或通过镊子,胎头吸引器可用于辅助分娩或剖宫产,以便尽快或通过捷径分娩孩子。
紧急剖宫产后,婴儿出生但被窒息。对于窒息的儿童,除保暖外,最重要的是清洁呼吸道,然后给氧。徐教授将孩子从手术台上的子宫中剪出,发现肤色和张力都不好。这就是我们在行业中经常说的话。紫色,有点软。
那天,新生儿科的值班医生很小。脐带断裂后,徐教授立即将孩子从手术台上带走,将孩子放在开放的保温箱中,用大毛巾迅速擦干身体,然后用嘴巴擦干。我用嘴里的吸管清洁了孩子的呼吸道。在生胎盘并清洁子宫腔的同时,我断断续续地关注孩子的情况。
孩子的呼吸道中有很多羊水。吸管的小缓冲罐即将装满。如果再次吮吸,则一定会将羊水和胎粪吸入嘴中。当时的情况是每一秒都很重要。她没有用新的吸管代替吸管,而是吐出了被吸入嘴里的羊水并继续吸。
然后,她用左手移动下颌,向后倾斜孩子的头,完全打开呼吸道,在孩子的鼻子和嘴上扣上氧气面罩,并开始给氧气加压。 1、2、3、4,在缝合子宫时,我通常会听到加压气囊的熟悉节奏,即5、6、7、8,共12次。我摘下面具的那一刻,哇,孩子哭了,身体红润。
电影中没有欢呼和欢乐,小护士没有时间跳起来。我们每个人都戴着无菌手套,并保护自己的工作。没有人会高五,没有人能停下来,更不用说放松了。音调的感觉。
徐教授迅速处理了脐带,问我舞台上发生了什么,子宫收缩是否良好。我说,很好,出血不多,而且缝合正在进行中。
由于新生儿暂时被窒息,徐教授表示最好将其送到儿科观察两天,应该没有大问题,也不会在以后推迟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录取。 。这时,我看到了她喜悦的微笑。她说,小张,你慢慢缝,让我和我的家人谈谈。
后来,在手术室的入口处,五岁和三岁大的家庭成员用一拳打了老太太的左锁骨。当我完成最后一根针时,老太太被送往外科病房。
在我没有时间换手术衣之前,我急忙去病房,看到老太太的瘦弱的身体依a在一张白色的大病床上,就像我瘦弱而干燥的祖母,像树叶一样,像风雨中的独木舟,她的眼睛仍然明亮,表情仍然沉稳。当她看到我时,她仍然拥有过去的微笑和保留,以及过去的平静和拒绝。我问我的鼻子和眼泪,疼吗?她说自己刚刚接受了止痛注射,但不久前并没有疼痛,但她的内心感到有些不适,很快就会好起来。
这位老妇人出院是因为她没有情人,没有孩子,只有一个远房的侄子。她仍然住在房山,每天都看不见她。我们病房的医生每天轮流照顾她。当人员不足时,实习医生和培训医生也参加了。
我最愿意在夏天的下午和她呆在一起而不说话。阳光照进她的房间,斑驳的阴影落在书和书架上,落在旧家具上。她仍然穿着棉衬衫。 ,她总是在读书,许多大猫在她身边,或者睡觉,或者要求鱼片,或者在柳条椅子上追逐自己的尾巴。
我说,你讨厌吗?
她说,不要恨。
我说,如果那天我出去解释我的病,我将无法打你。我年轻,骨骼强壮,估计不会骨折,皮肤最多也不会肿,两天就可以恢复正常。
她说,如果你打我,你就打。如果您打了您,即使您没有伤到它,您的心脏也会流血。您可能不再这样做了。我们已经老了,很快将无法做到。退出,那些孕妇呢?
从受伤中恢复过来后,老太太完全停止照顾病房。她只去了门诊。后来,她去了香港澳门中心上方的高档私人诊所。
我问,在那里工作很有趣吗?
她说,一般来讲,非常好,有钱的患者的素质更高。他们不会一直拉着医生的脖子。他们很吵。还有更多的外国人。他们听医生的话,从不讨价还价。还有一辆汽车载我上下班。现在我年纪大了,我不再想走路了。最重要的是,她对我小声说,还有很多钱养活那些大猫。
第一次,我看到她像小孩子一样天真狡猾地微笑。
从那时起,康科德妇产科的剖宫产不再受到严格的控制,因为我们确实不能保证每个孕妇都能顺利分娩,我们真的不能保证每个准妈妈都不会分娩。不受Ercha罪的约束。
后来,一些常用的分娩方法(例如用手转动胎头和镊子)逐渐消失了。
当病房的教授不在值班时,他们很少谈论病房的事务。社会正在越来越快地前进。每个人都开始关注他们的生活质量。谁愿意每24小时生活一次?此外,这项工作除惊险刺激外,还充满恐惧感。
这也锻炼了我们年轻一代的极端顽强的战斗能力。我在35岁时开始从事三线夜班工作。每天晚上,我都是整个医院中与妇产科有关的所有事务的指挥官和执行官。我用英语将其命名为CHO。
经历了激动人心的夜晚之后,我一直想像着东塘子胡同,瘦弱的老人,愿意随时聆听病房呼唤的老人以及一群大猫,是否仍然安全?您还在流浪和混乱的世界中感到羞辱吗? (本文作者张瑜是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副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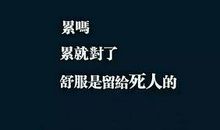 青少年励志句子
青少年励志句子 励志人生哲理的句子
励志人生哲理的句子 关于人生处事的励志语句
关于人生处事的励志语句 英语励志谚语带翻译
英语励志谚语带翻译 励志女人大气的句子
励志女人大气的句子 励志微信名字大全男
励志微信名字大全男 个性签名励志奋斗简单 励志个性签名简短霸气
个性签名励志奋斗简单 励志个性签名简短霸气 好听的励志句子简短
好听的励志句子简短 激励一生励志语录
激励一生励志语录 出去工作的励志句子
出去工作的励志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