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破落之街
萧红:断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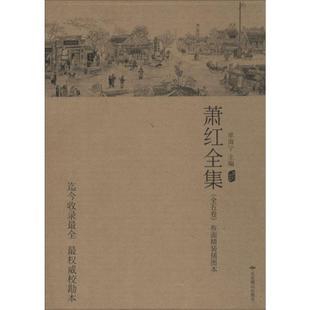
天空晴朗,白色的阳光将整个房间染成空旷。
让我们穿上衣服,折叠被子,系好自己的鞋带,然后我系好鞋带。他走到外面拍打脸,当他回来时,我愤怒地坐在床边。他已经忘记了手中的洗手盆,水溅到了地板上。他问我,我很生气,并给他看了鞋子。
鞋带被分成三部分,现在又被打破了。他再次解开鞋扣。我不知道他在做什么。我看着他环顾四周。他在找剪刀,但他没有买。他失望地用手扎了两根鞋带。
鞋带也应分为两部分,两个人应该绑鞋带。
他拿起桌上的铜板说:
“是这个吗?”
“不,我口袋里还有英里!”
他皱着眉头,那只是一角钱,他不想拿票。终于在楼下,他说:“我们应该吃什么?”
我的耳朵听他说话,我的眼睛看着我的鞋子。一种是白色的鞋带,另一种是黄色的鞋带。
秋风很紧,秋风的凄凉尤其在被破坏的街道上。
餐馆的墙壁上到处都是苍蝇,每个人都忙于饮食,没有闻到苍蝇的味道。
“老兄,我给我一分钱的辣椒白菜。”
“我要两美分的豆芽。”
有人再次大喊,哥们满头大汗。
“我再吃一斤蛋糕。”
苍蝇似乎呆在那里。我们就像其他人一样。我们不在乎卫生和体面。我认为女人不应该和一些讨厌的人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但是我吃了。
当我走出餐厅时,我很痛苦,好像要哭了,但我不能抱怨任何人。在工作日,他总是在吃完饭后问我:
“你吃饱了吗?”
我说:“我吃饱了!”其实,我还是有点不满意。
今天,他让我一个人上楼:“你进去!我在外面有事可做。”
仿佛他不是我的爱人,他转过身去楼下,离开了我。
在房间里,阳光不会落在墙壁上。它是一面灰色的四面墙,就像一个盒子或一个笼子。墙壁在逼迫我,使我的思想无用,并阻止我与他人接触或在世界上使用它的力量。 。
我不希望我的大脑扭曲,然后我再次入睡,拉着被子,在床上辗转反侧,仿佛我是个病人,我的肚子在尖叫,太阳落山了,它没有回来。我只吃了一碗麦片粥,还很早。
他回来了,只是自己一个人回来,没有bun头或其他东西来满足他的饥饿感。
我的肚子越来越响。我怕听肚皮的声音。我把肚子转到床上,压住了电话。
“你的肚子疼吗?”我说不,他再次问我:
“你生病了吗?”
我还是说不。
“天快黑了,那就去吃饭吧!”
他借钱了吗
“五分钱!”
泥泞的街道,沿路的屋顶密密麻麻地堆满了蜂窝,而平房的屋顶则催生了一层平房。它被钉住了,看上去像一幢建筑物,窗户关闭了,门关上了。但是那些在建筑物中出生的人却不像人类,他们是猪,是肮脏的羊群。我们来回时已经看到了这样的场景。现在,街道上一片泥泞,肚子在哭!我想碰上苍蝇,吃steam头。桌子对面的那个老人开始na。他可能是一个油壶。他的胡须被染成白色。无论他的衬衫还是袖口,都有油漆斑点。他用画手吃饭。我没有发现他不是在谈论卫生,因为我们在一起生活。
他大喊,他看到没有人在注意他。他像旧的旗杆一样举起木板凳,人们抬头看着他。毕竟,他不是叛乱的领袖,这是一个私事,在他的粥碗里睡着一只苍蝇。
每个人都笑了,笑了,他一定很神经质。
“我是个老人,你用苍蝇喂我!”他说,有点难过。
直到店主打电话给哥们给他换一碗稀饭,他才从木板凳上掉下来。但是他很孤独,摇头。
我们已经去过这条破旧的街道已有一年了。我们的生活技能比他们高。与他们不同,我们从水泥上爬出来。但是他们永远呆在那里,淹死了他们的生命,他们的子孙后代,但是什么时候会被淹死呢?
我们也是一只狗,就像其他没有心脏的狗一样。我们从水泥上爬出来,忘记别人,忘记别人。
1933.12.27

 好心情的经典语录
好心情的经典语录 经典成长语录
经典成长语录 问心无愧的经典语录 坦荡做人无愧于心句子
问心无愧的经典语录 坦荡做人无愧于心句子 迎接明天的经典句子 奋斗明天会更好的语句
迎接明天的经典句子 奋斗明天会更好的语句 主君的太阳经典语录
主君的太阳经典语录 盛世嫡妃经典语录
盛世嫡妃经典语录 成功人生规划经典格言
成功人生规划经典格言 2017经典励志格言
2017经典励志格言 墨子经典语录
墨子经典语录 爱神经典语录
爱神经典语录